大学生宿舍关系调查问卷(室同道合?一份包含MBTI的大学宿舍分配问卷背后)
(农健/图)
距离开学还有一周,2023年8月10日晚,北京理工大学知艺书院2023级115名本科新生收到一份问卷,内容包含MBTI、喜欢的“爱豆”(idol,指偶像艺人),以及作息习惯。这份问卷是为新生宿舍分配准备的。
第二天天还没亮,宿舍名单就出炉了。受委托设计问卷的是他们的学姐,知艺书院2022级学生吕嘉慧,她的设计初衷是,希望依据问卷结果把相同圈子的人聚集在一起,“让他们更快乐地度过大学四年”。
吕嘉慧自己的宿舍经历有些遗憾,舍友们爱好各自不同,“基本相当于没什么话聊”。
很快,这张问卷被发上社交媒体,“北理工宿舍分配统计MBTI”的话题登上热搜。
过去,高校的宿舍分配往往采取随机方式。如今,越来越多高校开始探索其他方法,MBTI只是最新的一种。南京大学、成都大学用问卷收集新生信息,再通过算法为他们分配或推荐舍友;而中国传媒大学、珠海科技学院(原吉林大学珠海学院)等一些学校将选择权完全交给学生,让学生自发组织,将写有自己生活习惯、性格与爱好的“简历”公开,用以寻找契合的舍友。
看似五花八门的分配方式,多多少少是为了规避可能发生的大学宿舍矛盾。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王青对大学宿舍关系有过研究,她觉得,“如果在编排宿舍时考虑到这些因素的话,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矛盾。”
宿舍矛盾背后又有另一番更深入的青年社交文化变迁。王青也认同:宿舍分配只能解决一部分矛盾。
“北理工宿舍分配统计MBTI”
这份宿舍分配问卷上,最受关注的问题便是MBTI,这是如今最流行的一种性格测试。
MBTI是迈尔斯-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的简称,测试结果由4个字母组成,指代一个人在注意力方向、认知方式、判断方式和生活方式4个维度上的倾向性。制定者是一对美国母女,她们的姓氏分别为布里格斯和迈尔斯,在这对非心理学专业背景的母女眼中,用四把标尺,就可以把复杂的人性归类成16种。
MBTI测试已被广泛应用在公司招聘和团队建设,但对它的科学性的质疑亦不断,有研究发现,一半以上人在隔了几周或一年多后重新测试,会得到不同的结果,因此其一致性、稳定性及可靠性存在缺陷。
为115名新生分配宿舍的吕嘉慧是“朋辈导师”,即在新生群内答疑解惑的学长。她相信MBTI的准确性。她的MBTI类型是“entj”,被称为指挥官型人格,这类人往往决策迅速,行动力强。仅用一个半小时,她就完成问卷设计,10日晚上七点半发出,11日凌晨四点半,全年级的宿舍分配结果就被发到了群里。
问卷很快被发到网上,8月12日,吕嘉慧发现,“北理工宿舍分配统计MBTI”词条在热搜榜挂了近十个小时,最高第二位。
除了MBTI,问卷被讨论的内容还包括是否打呼噜、说梦话、起夜、追星、“二刺螈”(二次元)等。
问卷也在北理工内部引发关注。“我(辅)导员的电话被其他院(辅)导员打爆了。”接着,问卷实现了校内普及,有人在吕嘉慧的社交媒体留言一张同款问卷截图:“经管书院也有啦!”
这股潮流还传到了更多高校。8月29日,广东财经大学智能财会管理学院一名学生发现,她所在学院为分配宿舍收集的问卷只包含MBTI类型,最后的分配结果,也主要以“i人”(内向)和“e人”(外向)区分。
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辅导员茹婧斐,则在自己的就业指导和心理健康课上寻找灵感。她设计的问卷除了MBTI,还有向毕业生征集的“宿舍生活中容易引发矛盾的问题”。
近年来,很多高校都开始拒绝过往的“开盲盒”方式,也就是随机分配的宿舍分配方案。
以往的宿舍分配,主要考虑将相同专业、班级,相邻学号的学生分在一起,而学号的排序通常参考姓氏拼音、笔画等。也有学校按照报到顺序安排宿舍。
2022年,成都大学让新生填写包含“你是社牛还是社恐”“你是否接受榴莲、螺蛳粉等异味食品”等问题的问卷,来为新生匹配舍友。同年,据兰州大学公众号介绍,为了“让同学们能选到自己志同道合的舍友”,一些学院推出了互选舍友的分配宿舍方法,学生像“写简历”一样在群内发布自我介绍和对舍友的期待,以此双向选择。电子科技大学2023级新生在网上自主选房时,可以查看某一房间中已选舍友的起床、睡眠习惯信息。
2023年9月16日,学长在浙江省湖州学院指引2023级新生办理报到手续。(视觉中国/图)
有i有e更有趣?
争议声也随之而来:用MBTI分到的舍友是否靠谱。
在吕嘉慧的构想中,MBTI并不是最重要的。她优先考虑的是问卷中一道关于“其他需求”的开放性填空题,之后的考量次序是:个人作息习惯、兴趣爱好,然后才是MBTI。
那道开放性填空题,有些人按提示填了想和谁在一起住,双方都愿意,就会被分在一起;有人填了“不想和追星的人在一个宿舍”。而通过收集到的问卷答案,吕嘉慧没法判断谁能接受这些预料外的需求,但她设置了一道关于“包容度”自评题,满分为5分——自评分数高的人,被认为有更大概率接受舍友的个性化需求。
在广东财经大学智能财会管理学院的宿舍分配中,一名新生观察到,配置大概是一个宿舍“两i两e”。
茹婧斐没有直接判断哪些人格适配,她提醒学生们考虑各自需要性格互补还是相似的舍友,又建议,“有i有e会让宿舍生活更加有趣”。
不同的分配方式与不同的需求相关,即便是在生源地这一指标上,不同人也有不同考量。西南政法地处重庆,茹婧斐不建议一个宿舍的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,并认为“一个宿舍里最好有一个川渝人,这样出去玩的时候会方便很多”。而吕嘉慧最害怕的,是南北饮食习惯差异,“吃不到一块就挺难受的”。
兰州大学主张“多元文化交融”,有学院规定“每个宿舍均有来自南方与北方的同学”“生源省份不少于3个”。“多元”还有另一层意味,2022年,该校法学院为了避免“早八”集体迟到,为每个宿舍分配了一位习惯早起的同学,担任着每个宿舍的“报晓公鸡”。
方案各有不同,但大部分设计者在意的点,其实是舍友之间能不能聊到一块。
“关起门来,宿舍就是一个圈子。”一个显著的对比是,吕嘉慧好朋友的大学宿舍全是“二次元”,能玩得很好;而她自己的舍友,有追韩娱的,有喜欢赛车的,“基本相当于没什么话聊”。
南京大学从2017年开始设置调查问卷,不仅统计兴趣爱好,还通过算法在不同爱好之间找到潜在关联。该校学生工作处老师郭亚敏曾向媒体介绍,“00后”兴趣爱好广泛,分散度高,学校的“隐语义模型”算法能够通过一些隐含特征,从学生已有的爱好,推算出他可能感兴趣的方面,再匹配室友,比如把喜欢戏剧的和喜欢历史的,喜欢生物的和喜欢物理的放在一起。
并且,南京大学的问卷每年都在调整,郭亚敏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,“孩子一代一代的,关注点不一样”。在2023年的问卷中,新生被问及舍友一起出去消费更倾向于AA制(所有人平均分担所需费用)还是轮流请客,能否接受舍友邀请其周末与朋友一起出行。
郭亚敏表示,“现在孩子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单独住的,一下子进入集体生活,总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。”而学校的做法是希望尽量减轻“不适应”,不要把差距过大的人分在一起。
一场宿舍关系干预实验
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王青,曾试图通过自己的实验找到一套大学宿舍关系磨合的方法论。
王青从2016年起担任了5年班主任,主动或被动地介入不少宿舍矛盾。有学生私下向她求助:和宿舍的某某关系很不好,造成了很大困扰。
2023年之前,江西财经大学采取班内随机的方式分配宿舍。到了2020年,王青决定抽取一部分宿舍,人为地干预宿舍关系的走向。
刚开始,考虑到人文学院女生多,王青决定先从女大学生宿舍入手。她在4个班级的大一女生中抽选了38名学生,以宿舍为单位,入学后每月开展1次“舍情相约”的小组活动,总共开展了三次。
后来却发现,男生的宿舍矛盾问题更严重,只是他们不善于求助。王青调研得知,男生宿舍肢体冲突率更高,亲密融合程度、对宿舍人际关系满意度也都低于女生宿舍。
活动的主题与宿舍关系的机制相关。王青分析,宿舍是公私属性混合在一起的空间,个人在里面吃饭、睡觉,但又把陌生人组合在一起生活。在这样的空间里,学生需要学习如何把握好尺度——什么是个人可以发挥的地方,什么是要尊重他人的地方。
第一次活动的主题就是公共秩序。王青模拟了一个场景:晚上11点,你很累了想睡觉,闭上了眼睛,舍友正在焦急地赶作业,噼里啪啦地打电脑。王青希望通过换位思考,让宿舍集体产生第一条公约:严格遵守作息制度,不干扰他人。
为此,她制定了一本27页的干预手册,当中规划了每一次活动的流程,其中提到“小团体”等常见的宿舍危机。她尝试引导学生思考,当这些情景发生在自己宿舍时,应该如何解决。
三次活动结束,学生的反馈达到她预期的效果。她们接受了两次测试,对比活动举办前后的宿舍人际关系质量发展,调查内容包括发生冷战、口角冲突等紧张的情况,以及宿舍内部的集体活动、情感交流情况,学生们还被问到,对宿舍关系的满意程度,和是否希望申请调换宿舍。
另有36名没参与过活动的女大学生,也接受了这项测试。两相比较下,王青得出结论:合适恰当的沟通干预,的确能够提前消除人际之间的矛盾与疏离。
2020年之后,王青不再担任班主任。而当了七年辅导员、带过1200多名学生的茹婧斐发现,大学生的宿舍矛盾问题越来越多,且趋向于在低年级爆发。她曾半夜被叫到学生宿舍处理一起打架事件,“能调和就调和,实在不行只有换(宿舍)”。
王青介绍,目前中国针对大学生宿舍矛盾的干预一般以事后修复、补救为主,从学校管理的层面来说,可以定期筛选出一部分关系不太好的宿舍进行干预。不过,王青也很清楚,随着时间推移,原本的干预所产生的效果,还是会越来越弱。
一个原因在于,新一代的学生,观念、心理和行为逻辑,都在发生变化。
卧谈会成传说
在如今的学校管理者构想中,对宿舍分配的干预,能更早避免一些可预见的矛盾。上海海洋大学一份对全国3875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,学生对宿舍关系不满意的主要原因依次是作息习惯、个人卫生、内/外向性格、是否玩游戏。
但干预宿舍分配并非一劳永逸,茹婧斐认为即使目前已经优化分配方式,也只可能解决作息这类表面矛盾。她和其他辅导员常讨论:学生的自我意识变强,接触的信息变多,都给宿舍关系带来变化。
一位辅导员和王青聊天时说到,70后、80后的学生会认为,舍友可能是人生里很重要的伙伴,不仅在读书阶段给人很大影响,毕业之后还能成为情感、事业上成长的助力。但现在,很多孩子进入大学以后有很明确的目标:保研、出国……从大一开始,他们就会遵从目标来安排自己的生活,不参与聚餐等集体活动,宿舍可能只是自己的歇脚地。
数字化也在加剧这种个体孤独。
约二十年前王青上大学时,手机还只用来打电话、发短信,那时很重要的宿舍活动是熄灯以后的卧谈,“现在孩子其实很多没有卧谈了,每个人都很忙,手机能满足很多需求,人和人之间的联系,亲密度、融合度就会降低很多。”
北京化工大学心理中心2019年曾对该校400名学生展开调查,80%以上的学生认为宿舍关系和谐,但将近一半的人承认在相处过程中存在摩擦。当被要求用一句话来描述宿舍关系时,40%选择了“亲如一家”,而更多人选择“普通朋友”。
不再担任班主任的王青,仍然对学生们的状况忧心。“每年(宿舍矛盾)都会出现,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偶然问题,有很大一部分群体在读书期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。”
吕嘉慧也拿不准分配宿舍的效果。她准备在9月中旬验证宿舍分配的效果,对愿意接受采访的新生进行线下或线上的匿名调查,问问他们与舍友相处得如何。
一些更尖锐的问题,靠宿舍分配无法规避。王青举例,比如宿舍里的两个人,正好是参评奖学金的两个人选,他们就可能有潜在的利益矛盾,此外,专业上的看法、为人处世等,也都可能引发冲突。
王青把2020年的这次实验写成《女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小组工作干预效果分析》一文,文章中她总结道: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质量在相处之初最高,后续会逐步变差。
一名学生对王青说过的话,让她印象很深:“舍友不是我朋友,我们只是搭伙在一起住宿而已。”
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陈宇龙
责编 吴筱羽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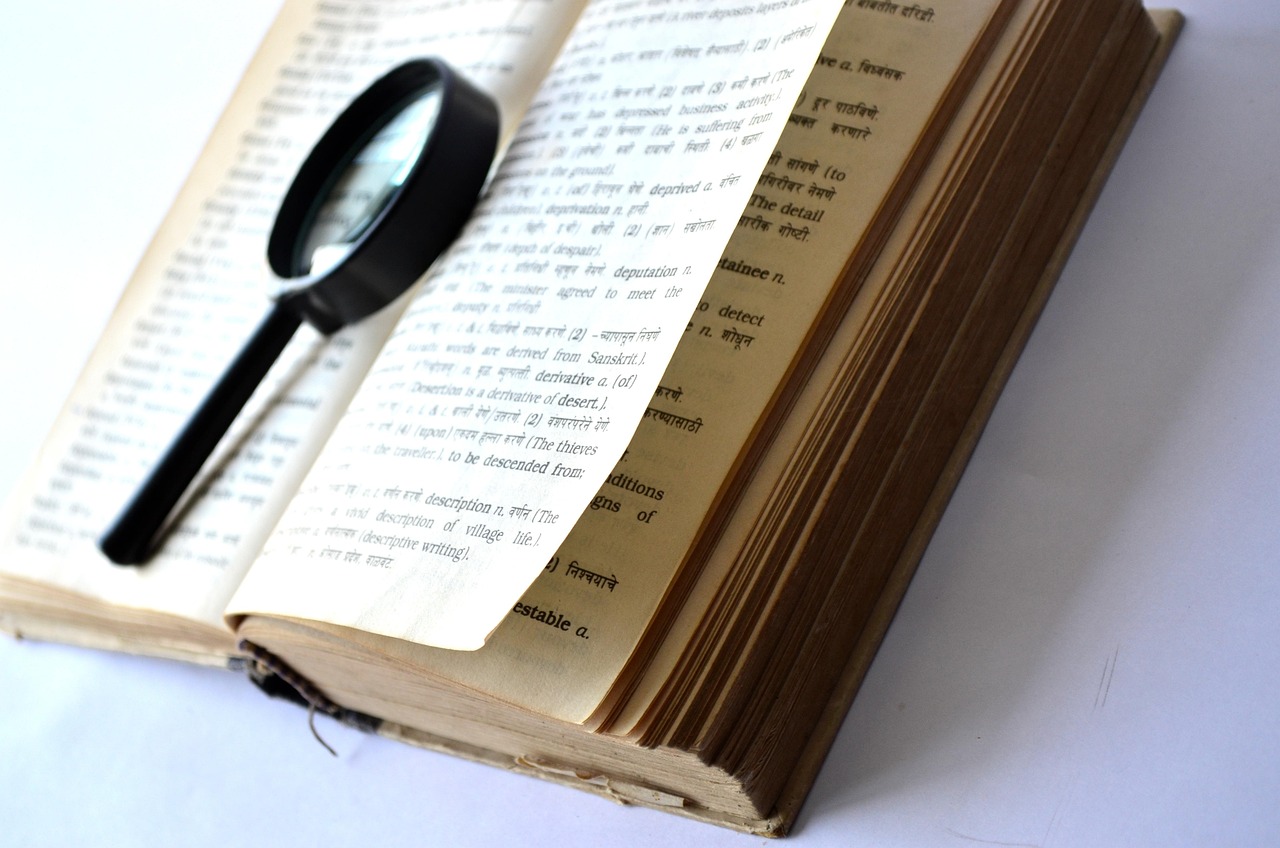

0 条评论